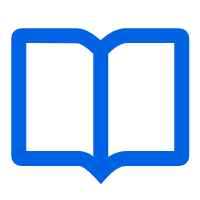铭的意思五行属什么?
《说文》云:“铭,记也。从金、名二文;会意。”即铭是铸在金属器物上用来记载事理的文字。故许慎认为“金文”即是“铭文”。 然而此说难以自圆其说,因为如果真是将文字铸在金属器物的表面,那么文字必然呈凸起的阳文形状,而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阴文。同时,如果真是直接将文字刻在金属器物上,则又很难解释,为什么后来这些青铜器被埋入土中以后,它们表面的文字能够保存下来而不消散。 现代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据显示,金文的呈现形式与商周时期人们的祭祀习俗密切相关。当时的贵族们进行祭祀时,首先要在地上铺上事先准备好的木板,然后在木板上放置要祭祀的尊彝等器皿(此类祭祀用的器皿通常无盖),最后把宰后的牲体陈放在器皿上。这样,当人们举行完祭祀仪式后,这些器皿以及上面的文字就都被掩埋在地下,只有少量出土。可见这种“置于器上”的金文,其实是一种阴文。 至于我们今人看到的青铜器上的金文,则是后人整理完成的。古人在对铜器进行加工时,首先要去除掉铜器表面的锈蚀和附着物,然后再打磨光润,最后涂上铅锡之类的合金,使之具有金属光泽并便于雕刻。但是这样处理过的铜器本身已经是平面了,无法再在上面镌刻凸起的文字。因此古人是先制作好刻字的陶范(铸造时的内模),然后把经过处理的铜浇铸到陶范里,使字刻在柔软的铜箔上,待冷却定型后再加以研磨抛光。这样的做法虽然能够在铜器表面得到凹凸相间的文字效果,但却不能完全达到直接铸印于器表的效果。于是古人便想出了另外的办法来弥补——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之上,又特制了一种涂有粘液的纸张覆盖在铜器表面,再用笔蘸着墨汁在纸上描摹刻字。纸的纤维结构使得它易于吸收笔墨的颜色,而又不易渗透,正适合用于复制精美的金文。 等到印刷术出现以后,古人就可以直接用纸来复印铜器上的金文了。
金文属于文字学范畴,跟五行没有任何关系。而五行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二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。
铭在康熙字典部首为金,说明在古代,多数的铭文都是镌铸在金属器物上的。文字因镌刻于金石上,其形体必然要方正精巧,且有庄重之感,故"金文""铭文"常常被人们联在一起。古人刻在或铸在金属器物上以称述功德内容的文字可称为"铭",这种文字一般比较短小。因此,在古文字中,"铭"与美相联系,如《说文·金部》:"铭,金也,从金属令声"。在字的构造上有明显的"金"字或从金属之字为其声旁的字都与金属有关,而以金属或其相关字为声旁的字亦多与美相关,如"铮、镇、钟、钲、铤、镯、铃、锒"等。所以,铭文在古文字中,就有金石、华美、庄重之义。
随着铭文镌铸载体的发展,人们进而将刻在石碑、木牌甚至竹简等非金属材质上的功德文字(如墓志铭)也纳入铭文的范畴。因受镌刻材料承载所限,此类铭文篇幅较大,记载内容也相对复杂。同时,作为镌刻体裁,铭文在体式上也有规范:"铭以自箴为义,故曰箴铭,其体有韵语,有散文,皆与箴同,惟韵语多用排比之词,铺张其事,与箴绝异。"(王增瑜《古代文体常识辞典》474页)所以,我们所讨论的铭的文体特征,主要是指这种篇幅较长、语言铺排且有韵语成分的文体。
铭体自产生以来,除少数碑铭是为他人撰写外,多为自作自铭。西晋刘勰最先在《文心雕龙·铭箴》中提出箴铭一体和"官箴"之说,但并未在文中作具体阐述。唐宋以后,文人们多以《铭箴》一"篇"和"官箴"之"箴、铭"相区分,即将《铭箴》中所涉及之"箴"与"铭"作文体上的界定和区别。在现代汉语中,"铭"字有三声,有作形容词和名词的发音,也有作动词的发音,如作"铭刻"、"铭记"解时,即为作动词用。而"箴"字只有作名词"箴言"释之意,没有或很少有作动词用。"箴"字在现代汉语中也没有作动词的情况,只有作名词用,如"箴言"。而"箴"作文体名称时,其体裁特点与现代汉语用法相似,均为形容词和名词。由于这种语言的同源性,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,西晋时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铭箴》中用"箴"字作自戒、自规文体名称时,与现代汉语的用法是一脉相承的。这样,我们就可将"官箴"之"箴"与铭箴一体之"箴"区分开了。
所以,我们所说"官箴"之"箴"与铭箴一体之"箴"是两种不同文体名称,二者不能混同。